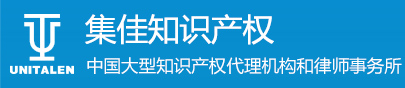- > 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 集佳周讯 > 2025年 > 集佳周讯2025年第39期 > 法眼观察 > 关于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认定
文/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印黄蕾
摘 要:市场交易不只局限于买卖关系,商业赠送本质上也属于商业活动。当赠品处于市场流通环节,消费者就有可能将其上贴附的标志作为商标识别,在赠品上使用商标也具有构成商标性使用的可能。在所有商标制度中,撤三与侵权制度与商标使用的关联最为密切,为厘清赠品上使用商标行为的定性问题,首先可以从撤三与侵权制度着手。经初步研究,撤三环节与制止侵权环节中商标使用的行为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在判断标准上亦存在区别。商标撤三制度涉及商标权这一排他性权利维持与否的问题,需严格围绕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有效发挥认定商标使用;商标侵权则涉及权益保护问题,需综合判断使用行为是否产生了混淆、淡化或破坏商标其他功能等损害,而需要被商标法所禁止。
关键词:赠品;商标使用;撤三;侵权;商标法
市场竞争背景下,折扣销售与免费赠送已成为经营者常用的营销策略。一方面,许多商家为谋求更多的交易机会,往往通过赠品、折扣等方式进行促销宣传。另一方面,鉴于我国并未建立防御商标及联合商标制度,对于一些防御性注册商标,权利人也期待通过在赠品上的小规模使用,对抗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而被撤销的风险。那么,在赠品上使用他人商标是否会侵犯他人商标权?在赠品上使用商标又是否能够在撤三程序中被认可?为厘清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下文将从维持商标注册角度的撤三制度与侵犯商标权角度的侵权案件两个维度,就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认定展开具体分析。
一、撤三案件中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认定
在2016年版《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下编第十一部分第七章“撤销注册商标案件审查审理标准”第5.3.5条第(3)项中,商标局曾将“仅作为赠品使用”列为不构成商标性使用的情形之一,后在2021年版《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中将该条款删除。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定性问题上,商标局不再单纯以有偿与否作为判断依据,而是与法院的观点逐渐趋同,结合个案情形,围绕商标性使用的要旨进行判断。经初步司法案例研究,在赠品上使用商标能否在撤三程序中获得认可,并产生维持商标注册的效力,往往可以综合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赠品的市场流通可能性是构成商标性使用的基础
商标作为一种商业标识,其识别和区分功能的发挥需要借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若贴附有商标的赠品仅为极个别终端消费者单独定制,或仅仅在企业内部流通,而无法进入市场,相关公众则难以知晓商标,商标的实际效用也将难以发挥。
例如在“震旦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震旦进修学院等商标权撤销复审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案”中,震旦行公司提交的《震旦月刊》《经营理念》等作为非公开出版物,无法证明这些内部刊物已进入流通领域,而能够为相关公众所知晓。因此法院并未认可其在内部刊物上的使用构成商标性使用。由于识别来源功能无从发挥,这类使用行为也将难以发挥维持商标注册的效力,而无法在撤三程序中被认可【1】。再如“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撤销复审案”中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仅证明三六一度公司存在一次赠送带有涉案商标植物摆件的行为,且赠品数量较少,缺乏证据证明其确实进入了市场流通环节。因此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植物”等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2】
与之相对,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等诉宋子豪撤销复审案”中,宋子豪在2012年4月至2012年12月,分别向上海市基督教国际礼拜堂、淮安市基督教堂、大同市基督教西堂、重庆市基督教协会等赠送了共计180本福音日记本。两审法院均认为,该类赠送行为虽无对价,但该行为与其他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处于市场流通环节中,并未影响其在市场流通环节起到来源识别功能。同时,涉案日记本除了赠送教堂外,也具有独立销售的可能性。综合上述事实,法院认定本案无偿赠送日记本的行为亦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真实、公开、合法的商标使用行为。【3】同样,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等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撤销复审案”中,两审法院均认为,江西恒大公司制作涉案1000枚“银质纪念章”,通常情况下是用于赠送客户或者对外销售。而无论是赠送还是销售,均为面向消费者的商业性使用行为。因此认定,在指定期间内,复审商标在贵重金属制纪念品上进行了使用,复审商标在该项商品上的注册应当予以保留。【4】
结合上述案例,若赠品仅为企业内部流通,则该使用行为通常难以在撤三程序中获得认可。而对于不向一般公众发售,仅向特定的个别消费者提供的赠品,法院往往会进一步依据赠品数量、规模等,进一步考察带有商标的赠品是否已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或存在进入流通领域的可能性,使得该商标能够为相关公众所知晓。
(二)识别来源功能的有效发挥是维持商标权利的关键
依据我国《商标法》第48条:“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从商标法理角度解释,商标作为一种商业标识,其首要功能在于使相关公众能够以商标为符号媒介,在商品与商品来源之间建立稳固联系。可以说,识别来源功能的有效发挥关系着一枚商标“成立与否”的问题,也是判断商标使用是否能够起到“维持商标注册效力”,并在撤三程序中获得认可的关键。
在“江西开心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复审案”中,开心人大药房虽然在向顾客赠送的洗洁精等生活用品上贴附了“开心人大药房”诉争商标,但在这些商品上同时也保留了原本的“雕牌”“立白”等商标。两审法院均认为,虽然开心人大药房在经营中将上述去污商品作为赠品赠送给消费者的行为,能够起到给开心人大药房连锁药店业务做广告的作用。但是消费者在接触到上述商品时,仍然能够清楚地识别出该商品来源于雕牌、立白洗洁精等商标的所有人,而不会认为其来源于开心人大药房。【5】
我国对商标采取“先注册原则”,权利人仅因为商标注册行为,就可以在核定的商品与商标两个因素之上,获得具有绝对性和支配性的排他权,这使得在撤三程序中对商标使用采取严格标准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即使商标使用发挥了广告功能,若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无法使消费者将使用人识别为商品来源,则这种行为也难以构成商标撤三制度所要求的商标性使用,从而无法维持商标的存续。
二、侵权案件中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认定
关于侵权案件中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认定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2条中指出:“搭赠是销售的一种形式,因此搭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是商标侵权行为,搭赠人应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明知或者应知所搭赠的商品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还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第26条中亦明确:“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附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属于商标法第57条第(3)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由于搭赠这类附条件赠与行为和销售行为密切绑定,赠品表面免费,实则与主商品打包在同一交易合同中,属于销售行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搭赠行为,实践中往往按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予以规制。
而对于纯粹赠与的行为性质,我国现行规则与司法口径虽未直接将其排除于商标性使用之外,但亦未像搭赠行为一样明确定性,仍然需要在个案实践中进行审查。依据目前司法实践,可初步整理出以下规则。
(一)有无对价并非阻却商标侵权的当然理由
市场交易不只局限于买卖关系,商业赠送本质上也属于商业活动。正如“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诉北京市顺义县致和腐乳厂侵犯商标权纠纷案”及“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蚌埠市禹会区金铂庄大酒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所指出的,发放和赠与一部分产品,是一种对外宣传自己产品的促销手段。涉案企业提供产品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销售和获利。【6】
只要赠品本身处于市场流通过程中,就依然能够发挥商品交换价值,有可能使相关公众认知商标,并通过商标识别商品的提供者。可以说,在市场交易背景下,赠品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侵权案件中商标性使用的认定标准不应仅由于商品有无对价而有所区别。当赠品能够处于市场流通之中,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定性应与一般商品采取相同标准。
(二)商标使用的含义在侵权案件中更为丰富
我国《商标法》将商标使用的定义安排在第六章“商标使用的管理”部分,无论撤三还是侵权案件均会引用该条定义。对于撤三制度中的“商标使用”与侵权案件中的“商标使用”是否应作等同理解,采取同一判断标准这一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商标授权确权的司法审查》一书中指出,撤三制度中的商标使用不宜采取过于宽松的判定标准,否则将给他人积极利用有限的商标资源造成过多障碍;而商标侵权判定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防止混淆或者淡化,凡可能导致混淆或者淡化的使用方式都有可能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而被禁止。【7】由于维持注册与制止侵权作为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趣旨,“商标使用”在解释论上并不相同【8】,在判断标准上亦应存在区别。
前文我们提到,一个标志是否有效发挥了识别来源功能,决定着一个商标“维持与否”的问题。而随着商标的不断使用,品牌商誉不断累积,商标在识别来源功能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品质保障和广告宣传等其他功能,一枚商标所蕴含的价值将不断丰富。商标侵权制度不仅保护商标本身,更是保护商标上附着的声誉。即使只发生了少量的商标使用行为,亦可能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即使消费者将商品与商品来源正确联系,亦可能损害商标的质量保障、广告宣传等其他功能,损害商标声誉,从而需被商标法所禁止。
目前围绕无条件赠与商标侵权领域的相关案例较少,但是在商品销售领域,已存在许多司法案例对商标的其他功能予以保护。例如“不二家”案中,虽然行为人在产品分装时系将“不二家”商标贴附在“不二家”品牌生产的糖果包装上,消费者能够准确识别商品提供者,并未破坏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但由于分装行为对商标品质保障功能产生了影响,法院依然认为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9】前文已经论述,有无对价并非阻却侵权的当然理由,当赠品能够处于市场流通之中,在赠品上使用商标行为的定性应与一般商品采取相同标准。若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对商标造成了混淆、淡化或破坏了商标质量保障、广告宣传功能,对商标声誉产生了损害,特别是当赠品系向不特定公众派发或者已经实际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同样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三、总结
有无对价并非判断商标使用行为性质的关键,也不能因无偿性就否认赠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市场交易不仅仅局限于买卖关系,商业赠送本质上也属于商业活动。只要带有商标赠品本身处于市场流通过程中,就有可能使相关公众认知商标。
对于在赠品上使用商标的行为性质认定问题,应当依据商标各项制度的不同趣旨,判断赠品是否能够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并分析该使用行为是否能够有效发挥识别来源功能,从而能够产生维持商标注册的效力;抑或是该使用行为对商标声誉产生了损害,而需要被商标法所规制。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5971号行政裁定书。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4907号行政判决书。
【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高行终761号行政判决书。
【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行终2424号行政判决书。
【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131号行政判决书。
【6】参见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20)皖0304民初1183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中民终字第1998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编著:《商标授权确权的司法审查》,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399-400页。
【8】张鹏:《<商标法>第49条第2款“注册商标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评注》,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2期,第3页。
【9】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知初字第416号。